近日,特斯拉事件持續發酵,又將智能電動汽車的安全問題頂上熱搜。雖然車輛失控可能由于多種原因,目前也尚未有官方定論,但從一定程度上說,特斯拉目前面臨的問題也是智能電動汽車發展到現階段所面臨的問題。管中窺豹,我們當以此為鑒,深入客觀探究智能電動汽車的安全管理問題。
“近年來,我國每年都會發生10余起電動車失控類交通事故,其中有營運車輛,也有非營運車輛。”近日,交通運輸部公路科學研究院汽車運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周煒接受《中國汽車報》獨家專訪時說,“在今年,電動公交車失控事件時有發生,其中某起事故中,車輛失控超過兩公里,在撞到其他車輛和路側固定設施后才停了下來。”
周煒作為國務院事故調查組成員,參與過多起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交通事故的調查工作。對于特斯拉剎車失靈事件,他表示不了解相關情況,不便做出評論。但他表示,交通運輸行業更多關注的是營運車輛的運行安全性問題,從對多起電動公交車失控事故的分析來看,制動失控通常發生在起步后持續加速現象下。“我們認為智能電動車的可靠性以及控制策略還有待改進和完善,不能把事故的一切責任推到司機身上。”他說。
我國智能汽車發展已經進入落地推廣應用的新階段,尤其是ROBOTAXI、ROBOBUS等高級別無人駕駛營運車輛在國內公開道路上陸續投入運營,從技術管理、安全生產管理和實際使用角度考慮,周煒認為,推動智能車輛落地應用需要解決六大障礙。
從控制策略和可靠性角度出發尋找原因
“公交車作為營運車輛,其司機都是職業駕駛員,他們拿到最高級別的A1駕照經過了千錘百煉,專業能力和駕駛操作水平值得信賴。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車輛長時間無法剎停,就說明是車輛本體問題而非駕駛員操作問題。”周煒分析,智能電動汽車的制動失控,可能是多方因素耦合條件下激發,系突發性失控,不具備一定規律性,是相對復雜的問題。
“車輛的控制策略、機械可靠性、電池可靠性、電動車高電壓特性帶來的電磁干擾,以及氣候環境因素等都可能造成事故。”周煒說,我們首先要對國內外所有相關事故進行深度研究,基于大量事故案例進行分析和判斷,排除事故中存在的歧義和誤解,找到本質性的、有特征和規律性的問題,然后從車輛本體控制策略和可靠性角度出發尋找原因,找到了原因,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智能車輛控制策略應以減速停車為第一原則
各企業自動駕駛的控制策略具備一定差異性,這涉及到各企業核心算法和底層邏輯的不同。周煒指出:“無論算法有何不同,最基本的應該是保證底層邏輯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從用車角度來講,無論發生任何事情,減速停車都應該是第一原則。”
基于此思路,對智能車輛的控制策略進行統一是當務之急,有關部門需盡快完成標準編制和發布,推動輔助駕駛或無人駕駛技術標準的統一。
“在推動輔助駕駛時,自動緊急制動系統(AEBS)非常重要。這里的控制策略涉及到人、車優先級的問題。”周煒說。比如歐洲ECE R131制動性能法規是操作者優先策略,即只要駕駛員介入,AEBS就取消工作。“比如人不小心碰到方向盤或是踩了油門,導致AEBS取消減速或是反而加速,就可能導致危險發生。”周煒認為,這一策略優先級是有問題的,違背了車輛行駛的路權原則。
“AEBS自動剎車的力度遠大于人踩剎車的力度。”周煒介紹,我國《營運車輛自動緊急制動系統性能要求和測試規范》JT/T 1242要求確保AEBS的最優制動效果,這是提倡“以人為本”的中國思路和中國方案,也逐漸被ECE、ISO等國際上相關組織認同。
厘清概念和發展思路是第一要務
周煒認為,智能車輛的發展存在幾個比較嚴重的誤區,包括概念定義和發展思路等。
首先是,關于自動駕駛分級的劃分和理解。周煒表示,一是L0-L5的SAE分級是基于主動安全系統的智能化,而不是整車的智能化分類,這種劃分相對片面;比如作為單一工況應用,自動泊車系統達到L4等級不能代表車輛整體達到了L4等級。二是行業基于車輛開發和制造角度對自動駕駛分級的技術理解存在誤區;他特別指出,站在用車角度,L3級別的人機共駕存在明顯問題,因為人類有限的注意力無法做到全神貫注地隨時準備進行秒級以內的突發狀況接管。
其次,安全員的定義不準確、不科學。他指出,無論是國際和國內對駕駛員的定義都非常明確,駕駛員是法律上規定的責任主體,沒有駕駛證的人員坐在駕駛員的法定位置上屬于違法駕駛,不能用安全員的名目掩蓋法律上的主體責任。
第三,車輛的智能化和智能車輛不能同一而論,概念的界定要厘清。
周煒舉例解釋這兩個概念:“車輛的智能化是傳統車企將智能化技術和智能化理念賦能于傳統車輛,車輛本身的功能性能和形態不變,也就是車+AI,是推動車輛技術發展的一種路徑;智能車輛則更多是由非傳統造車勢力遵循與傳統車企完全不同的思路所打造的產品,比如某些互聯網造車企業是在試圖實現所有電腦功能的條件下,增加人或貨物的運載功能,將電腦以車的形態生產出來;另外,還有一些產品生產商處于兩者之間,他們也具備一定的互聯網思維,但更多是體現產品的設計、研發和生產。”
遵循不同的思路和理念,所造出的產品也就體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基于此,周煒認為當前的造車企業可以分為三類:傳統造車、互聯網造車、融合二者思維和理念的造車。
立足使用者角度造車 而非產品
第四,造智能車輛不難,打造其使用環境和生態則是很長久的過程。“當前國內外很多企業都是立足于產品思維造車,沒有從汽車使用者的角度考慮,這一思路需要調整。”周煒指出。智能車輛最終要應用于交通運輸行業,我們需要將使用環境和有限條件結合起來,以系統性的思路去看待它的發展。
周煒指出,智能車輛的使用是車輛本體條件和使用環境條件的耦合,二者是此消彼長的過程,相互促進、相互博弈,使用條件低則車輛智能化程度高,使用條件高,則車輛智能化程度相對可以低。也就是說,隨著車路協同技術發展,當路端環境條件足夠智慧化,單車智能化程度甚至可能會下降。
根據使用條件和無人駕駛的耦合程度,《中國營運車輛智能化運用發展報告(2020)》(以下簡稱《報告》)將無人駕駛的運用分為三類情況:完全封閉區域,可以實現條件非常高的無人駕駛;有限開放條件下的無人駕駛;無條件無人駕駛,全面開放無人駕駛。基于此劃分,周煒指出,目前市場上所有的無人駕駛都是有條件的無人駕駛,或者說是高級智能輔助駕駛,到實現完全的無人駕駛還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測試。
周煒認為,正是無條件使用的技術路線誤區,造成了特斯拉等企業容易出現掛一漏萬、以偏概全,導致較高的使用安全風險。
合理劃分和定義自動駕駛技術路線
第五,未來智能車輛的發展和管理必須合理劃分和定義自動駕駛技術路線。比如將輔助駕駛和無人駕駛做出明確區分。因為無人駕駛車輛在形態上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其功能和性能相應變化,相應約束傳統車輛的標準和法規都不再適用,需要大范圍調整。
“比如無人駕駛車輛還需要遵循碰撞法規嗎?融合了客運車輛和貨運車輛,無人駕駛車輛相當于一個底盤扣上載人的殼子是客車,扣上載貨的殼子是貨車,更加模塊化和更具靈活性。”周煒解釋說。
《報告》將以人為駕駛控制主體的輔助駕駛車輛和以車輛為駕駛控制主體的無人駕駛車輛劃分為五類:輔助駕駛以智能化技術介入駕駛的程度分為預警類輔助駕駛(G1)和控制類輔助駕駛(G2);無人駕駛則以運用風險程度和運用難度,按照智能化運用空間分為封閉區域無人駕駛(G3)、有限開放區域無人駕駛(G4)和開放區域無人駕駛(G5)。
智能汽車生態尚未形成 六大使用障礙待解決
“我國智能汽車發展從2015年啟動試點示范至今已有5年多,依然處于以生產企業為主的試點示范階段,生產端一頭熱,使用端不會用、不敢用,沒有形成很好的生態。”周煒指出。
在周煒看來,我國智能汽車的使用當前面臨著六大障礙:政策法規以試點示范為主,不涉及責任主體劃分;標準規范不綜合、不落地,缺乏中國思路和中國方案;只考慮新車制造和生產,未考慮和不重視在用車維保問題,在用車使用缺乏標準規范支持;網絡安全問題;基礎設施環境條件發展不均衡、不系統;測試評價不科學不合理。
“車路協同的本質包括物理協同、信息協同和管理協同,勢必要統籌發展。我們現在只提了信息協同,物理協同和管理協同沒有跟上。另外,當前的現狀是車端一頭熱,路端冷眼觀望,無法形成系統化、體系化。”周煒說,這就無法保障實際使用的推進。
在測試評價體系方面,周煒認為,當前全球范圍內對于智能汽車的測試評價的思路、手段和方法都存在誤區,比如基于無條件使用的技術路線誤區將“復雜問題復雜化”。“行業現在要做的是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立足使用角度,偏重整車性能和整車功能的測試評價。”他說。
最后,周煒給出了三個結論:
第一,智能車輛的有條件使用是當下最現實的問題,不鼓勵智能車的無條件使用;
第二,一直在試點示范階段的智能車輛無法實現盈利,智能車輛的實際落地運用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關乎汽車及相關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智能汽車的使用需要解決一系列障礙,表現在前述六大障礙,每一個障礙都要力量均衡地解決,不可偏廢。
“近年來,我國每年都會發生10余起電動車失控類交通事故,其中有營運車輛,也有非營運車輛。”近日,交通運輸部公路科學研究院汽車運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周煒接受《中國汽車報》獨家專訪時說,“在今年,電動公交車失控事件時有發生,其中某起事故中,車輛失控超過兩公里,在撞到其他車輛和路側固定設施后才停了下來。”
周煒作為國務院事故調查組成員,參與過多起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交通事故的調查工作。對于特斯拉剎車失靈事件,他表示不了解相關情況,不便做出評論。但他表示,交通運輸行業更多關注的是營運車輛的運行安全性問題,從對多起電動公交車失控事故的分析來看,制動失控通常發生在起步后持續加速現象下。“我們認為智能電動車的可靠性以及控制策略還有待改進和完善,不能把事故的一切責任推到司機身上。”他說。
我國智能汽車發展已經進入落地推廣應用的新階段,尤其是ROBOTAXI、ROBOBUS等高級別無人駕駛營運車輛在國內公開道路上陸續投入運營,從技術管理、安全生產管理和實際使用角度考慮,周煒認為,推動智能車輛落地應用需要解決六大障礙。
從控制策略和可靠性角度出發尋找原因
“公交車作為營運車輛,其司機都是職業駕駛員,他們拿到最高級別的A1駕照經過了千錘百煉,專業能力和駕駛操作水平值得信賴。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車輛長時間無法剎停,就說明是車輛本體問題而非駕駛員操作問題。”周煒分析,智能電動汽車的制動失控,可能是多方因素耦合條件下激發,系突發性失控,不具備一定規律性,是相對復雜的問題。
“車輛的控制策略、機械可靠性、電池可靠性、電動車高電壓特性帶來的電磁干擾,以及氣候環境因素等都可能造成事故。”周煒說,我們首先要對國內外所有相關事故進行深度研究,基于大量事故案例進行分析和判斷,排除事故中存在的歧義和誤解,找到本質性的、有特征和規律性的問題,然后從車輛本體控制策略和可靠性角度出發尋找原因,找到了原因,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智能車輛控制策略應以減速停車為第一原則
各企業自動駕駛的控制策略具備一定差異性,這涉及到各企業核心算法和底層邏輯的不同。周煒指出:“無論算法有何不同,最基本的應該是保證底層邏輯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從用車角度來講,無論發生任何事情,減速停車都應該是第一原則。”
基于此思路,對智能車輛的控制策略進行統一是當務之急,有關部門需盡快完成標準編制和發布,推動輔助駕駛或無人駕駛技術標準的統一。
“在推動輔助駕駛時,自動緊急制動系統(AEBS)非常重要。這里的控制策略涉及到人、車優先級的問題。”周煒說。比如歐洲ECE R131制動性能法規是操作者優先策略,即只要駕駛員介入,AEBS就取消工作。“比如人不小心碰到方向盤或是踩了油門,導致AEBS取消減速或是反而加速,就可能導致危險發生。”周煒認為,這一策略優先級是有問題的,違背了車輛行駛的路權原則。
“AEBS自動剎車的力度遠大于人踩剎車的力度。”周煒介紹,我國《營運車輛自動緊急制動系統性能要求和測試規范》JT/T 1242要求確保AEBS的最優制動效果,這是提倡“以人為本”的中國思路和中國方案,也逐漸被ECE、ISO等國際上相關組織認同。
厘清概念和發展思路是第一要務
周煒認為,智能車輛的發展存在幾個比較嚴重的誤區,包括概念定義和發展思路等。
首先是,關于自動駕駛分級的劃分和理解。周煒表示,一是L0-L5的SAE分級是基于主動安全系統的智能化,而不是整車的智能化分類,這種劃分相對片面;比如作為單一工況應用,自動泊車系統達到L4等級不能代表車輛整體達到了L4等級。二是行業基于車輛開發和制造角度對自動駕駛分級的技術理解存在誤區;他特別指出,站在用車角度,L3級別的人機共駕存在明顯問題,因為人類有限的注意力無法做到全神貫注地隨時準備進行秒級以內的突發狀況接管。
其次,安全員的定義不準確、不科學。他指出,無論是國際和國內對駕駛員的定義都非常明確,駕駛員是法律上規定的責任主體,沒有駕駛證的人員坐在駕駛員的法定位置上屬于違法駕駛,不能用安全員的名目掩蓋法律上的主體責任。
第三,車輛的智能化和智能車輛不能同一而論,概念的界定要厘清。
周煒舉例解釋這兩個概念:“車輛的智能化是傳統車企將智能化技術和智能化理念賦能于傳統車輛,車輛本身的功能性能和形態不變,也就是車+AI,是推動車輛技術發展的一種路徑;智能車輛則更多是由非傳統造車勢力遵循與傳統車企完全不同的思路所打造的產品,比如某些互聯網造車企業是在試圖實現所有電腦功能的條件下,增加人或貨物的運載功能,將電腦以車的形態生產出來;另外,還有一些產品生產商處于兩者之間,他們也具備一定的互聯網思維,但更多是體現產品的設計、研發和生產。”
遵循不同的思路和理念,所造出的產品也就體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基于此,周煒認為當前的造車企業可以分為三類:傳統造車、互聯網造車、融合二者思維和理念的造車。
立足使用者角度造車 而非產品
第四,造智能車輛不難,打造其使用環境和生態則是很長久的過程。“當前國內外很多企業都是立足于產品思維造車,沒有從汽車使用者的角度考慮,這一思路需要調整。”周煒指出。智能車輛最終要應用于交通運輸行業,我們需要將使用環境和有限條件結合起來,以系統性的思路去看待它的發展。
周煒指出,智能車輛的使用是車輛本體條件和使用環境條件的耦合,二者是此消彼長的過程,相互促進、相互博弈,使用條件低則車輛智能化程度高,使用條件高,則車輛智能化程度相對可以低。也就是說,隨著車路協同技術發展,當路端環境條件足夠智慧化,單車智能化程度甚至可能會下降。
根據使用條件和無人駕駛的耦合程度,《中國營運車輛智能化運用發展報告(2020)》(以下簡稱《報告》)將無人駕駛的運用分為三類情況:完全封閉區域,可以實現條件非常高的無人駕駛;有限開放條件下的無人駕駛;無條件無人駕駛,全面開放無人駕駛。基于此劃分,周煒指出,目前市場上所有的無人駕駛都是有條件的無人駕駛,或者說是高級智能輔助駕駛,到實現完全的無人駕駛還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測試。
周煒認為,正是無條件使用的技術路線誤區,造成了特斯拉等企業容易出現掛一漏萬、以偏概全,導致較高的使用安全風險。
合理劃分和定義自動駕駛技術路線
第五,未來智能車輛的發展和管理必須合理劃分和定義自動駕駛技術路線。比如將輔助駕駛和無人駕駛做出明確區分。因為無人駕駛車輛在形態上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其功能和性能相應變化,相應約束傳統車輛的標準和法規都不再適用,需要大范圍調整。
“比如無人駕駛車輛還需要遵循碰撞法規嗎?融合了客運車輛和貨運車輛,無人駕駛車輛相當于一個底盤扣上載人的殼子是客車,扣上載貨的殼子是貨車,更加模塊化和更具靈活性。”周煒解釋說。
《報告》將以人為駕駛控制主體的輔助駕駛車輛和以車輛為駕駛控制主體的無人駕駛車輛劃分為五類:輔助駕駛以智能化技術介入駕駛的程度分為預警類輔助駕駛(G1)和控制類輔助駕駛(G2);無人駕駛則以運用風險程度和運用難度,按照智能化運用空間分為封閉區域無人駕駛(G3)、有限開放區域無人駕駛(G4)和開放區域無人駕駛(G5)。
智能汽車生態尚未形成 六大使用障礙待解決
“我國智能汽車發展從2015年啟動試點示范至今已有5年多,依然處于以生產企業為主的試點示范階段,生產端一頭熱,使用端不會用、不敢用,沒有形成很好的生態。”周煒指出。
在周煒看來,我國智能汽車的使用當前面臨著六大障礙:政策法規以試點示范為主,不涉及責任主體劃分;標準規范不綜合、不落地,缺乏中國思路和中國方案;只考慮新車制造和生產,未考慮和不重視在用車維保問題,在用車使用缺乏標準規范支持;網絡安全問題;基礎設施環境條件發展不均衡、不系統;測試評價不科學不合理。
“車路協同的本質包括物理協同、信息協同和管理協同,勢必要統籌發展。我們現在只提了信息協同,物理協同和管理協同沒有跟上。另外,當前的現狀是車端一頭熱,路端冷眼觀望,無法形成系統化、體系化。”周煒說,這就無法保障實際使用的推進。
在測試評價體系方面,周煒認為,當前全球范圍內對于智能汽車的測試評價的思路、手段和方法都存在誤區,比如基于無條件使用的技術路線誤區將“復雜問題復雜化”。“行業現在要做的是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立足使用角度,偏重整車性能和整車功能的測試評價。”他說。
最后,周煒給出了三個結論:
第一,智能車輛的有條件使用是當下最現實的問題,不鼓勵智能車的無條件使用;
第二,一直在試點示范階段的智能車輛無法實現盈利,智能車輛的實際落地運用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關乎汽車及相關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智能汽車的使用需要解決一系列障礙,表現在前述六大障礙,每一個障礙都要力量均衡地解決,不可偏廢。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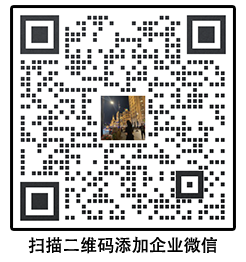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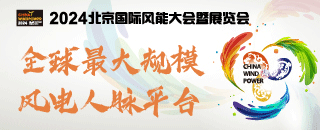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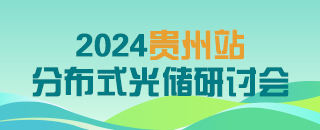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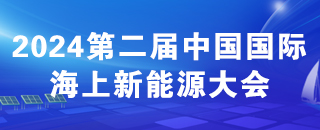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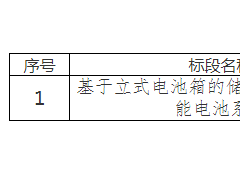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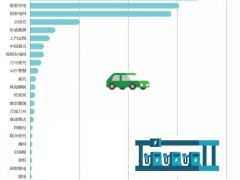

0 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