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底,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分時電價機制的通知》,要求各地劃分峰谷時段,確定電價價差。之后2年多的時間,各省地區陸續出臺并且持續調整了電價終端銷售價格,普遍或者有選擇地區分了分時、季節、尖峰與低谷的電價水平。
從目前積累的用電數據以及與實施峰谷電價之前的用電行為比較,這一定價機制明顯地改變了用戶用電行為,需求特性(profiles,需求水平隨著時間的變化)呈現明顯的價格彈性。
從價格手段的視角,這一變化符合政策預期;但是從價格機制的視角,也就是“新的定價是否反映了用電的社會真實邊際成本”來看,答案更加復雜。這尤其需要程度上的精確考量,既不偏高也不偏低。
有新聞報道稱:多地引入中午時分的低谷價,用電用戶響應之后,中午時分的需求反彈明顯。“現貨谷段(10: 00—15: 00)平均電價同比提升17%以上,晚間峰段(17: 00—22: 00)平均電價同比下降10%”。由于光伏出力大部分處于這一“低谷電價”時期,使得可預期比較的發電收入(或者減少的避免電力支出)大幅下降,新建項目往往需要重新評估投資回收前景。
本文中,我們聚焦部分省份的峰谷電價安排,討論這種峰谷電價拉大價差“粗尺度”的事實及其影響。這種用力過猛,造成極具長期競爭力的光伏發電反而瞬間缺失了足夠投資回收機會,從而形成相比“最優節奏”(反事實基準線)更慢的容量增加,有可能影響整個系統轉型的進度。
更進一步,我們希望可以探討粗尺度電價機制的不足,并提出進一步解決方案應走的路徑。
事實匯總:多地午間低谷電價設定
從技術上來說,分時電價通常只在幾個時間步長內有所不同,而且是提前很長時間確定的。同時,分時電價適用于整個用戶群體,在較長時間(比如超過1年)內保持穩定不變,仍舊屬于行政定價的范疇。
從時空分辨率和提前量時間來看,它們或多或少只是“真實”(反映供需關系,也就是電力價值)價格的粗略近似值。在多大程度上近似,成為一個超越科學的藝術問題,也為各種自由量裁提供了空間。
在我國,各地陸續出臺了深谷電價政策。具體方案,相比平段下降幅度、覆蓋用戶群體、具體執行月度時間等方面存在各種各樣的差異。但是總體而言,這些降價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調整的僅是發電價格部分。相比年度基準電價,大部分下調程度在20%—50%,山東高達90%。而其他“固定”部分,比如各種輸配加價、政府基金、線損(這個是應該同向變化的)等保持不變,從而代表終端電價10%—50%的下降。
第二,調整的往往只是終端價格,不同時間的重新價格分配,與上游批發價格無關系。直覺上來看,低電價對煤電是受損的,這2~3個小時的發電都無法覆蓋燃料成本。但是,實際上并不是這么回事。一方面,發電端的價格是中長期合同交易以及短期合同交易的價格,往往并不具有這樣高的時間分辨率。而各地的現貨(日前、實時)交易試點,也并不存在跟終端電價聯動的機制。這一價格調整僅限于終端,本著“收益中性原則”的紙面調整,影響不同時間用戶用電的支付水平,不涉及上游價格變化。這一變化僅為終端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第三,從“影子價格”視角,這種調整跟系統的發電成本不一致的程度更大了。行政管制基準電價或者電網代理購電平均價格與煤炭價格高位情況下,總體上煤炭發電就處于盈虧平衡點或者略微損失的地步。進一步的降價使得“計劃內”發電在這些時刻更加不反映邊際成本。而計劃外市場交易購電價格,理論上發電商可以根據成本動態預期進行定價。但是由于存在各種上下限與對計劃內價格的參照要求,這方面的選擇其實也相當有限。
回到起點:我國大部分地區仍舊是煤電占主導的系統
從發電的社會邊際成本來看,煤電在大部分時間(如果不是全部)構成了邊際機組。電價的波動,從理論上講,也僅限于煤電內部的成本差異(比如發電煤耗的差別)。此外,有兩個特別的因素也構成了我國電力批發價格不應該波動特別劇烈的原因。
第一,過去我國進行了大范圍大規模的“上大壓小”,以及后續的持續改造工作,使得不同歷史時期建設的機組差別進一步縮小。有研究顯示:南方五省(廣東、廣西、云南、貴州、海南)煤電機組的平均發電標準煤耗305.6克標準煤/千瓦時,而地方國企煤電機組標準煤耗311.8克標準煤/千瓦時。雙方只有不到6克標煤(2%)的差別。當然,這是兩個群體總體平均地比較,機組的總體差異會比這個大不少,但是煤耗也肯定不達到差別50%的程度。如果只是基于此來看,午間降價到90%的程度,屬于超調。
第二,我國物理裝機在解決了“資金不足”的問題之后,一直是過剩的狀態。這意味著即使存在新的需求,它也不大可能有新的投資需求,也就是不意味著極高的邊際成本,包括建設成本。有文章的主觀預測結果不經意間顯示了2022年的確切現狀:“2022~2035年,火電裝機與最大用電負荷比值預計由1.07下降到0.77左右,火電最大出力與最大用電負荷比值預計由0.84下降到0.66左右”。
這充分表明:起碼現在,火電裝機還是比最大負荷高7%以上的。此外,必須特別強調的,目前存在的機組出力不足問題,很多時候在于缺乏足夠發電意愿,而不是物理裝機。因此,“保供”話題也必須針對不同的情況,給予對待。
午間低谷電價形成了對(分布式)光伏的定向“阻擊”
光伏日照強烈的時候發電多,有日照的時候發電,而無日照的時候不發電。基于浙江天氣的典型光伏發電曲線表明:光伏的年平均利用因子在11%,滿負荷等價小時數1000小時左右,中午11:00-14:00 3個小時的發電量往往占到總發電量的70%,甚至更多。

圖1 光伏發電主要集中在中午的11:00-14:00
即使光伏很多,煤電仍舊在午間是邊際機組,價格也不應該低到基準50%,甚至更甚的程度。這一特別的價格下降,更像是一種價格手段,將光伏發電的“影子價值”(參照系)人為降低,從而抑制了新增光伏的價值,對其投資回報產生了影響。
準確地講,受到直接影響的是在配網側的分布式光伏。
這一點,與國外往往并不具有可比性。典型的就是美國(USA)加州的所謂“鴨子曲線”變成“深谷曲線”的問題。加州光伏發電比例已經超過總用電量的30%,并且該州一度推行的凈能量計量(NEM)政策為住宅光伏發電提供大量隱性補貼,使得光伏在經濟最優意義上“已經過剩”。
它的中午的凈負荷(net load)往往是零,甚至進入負的區間。這對于我國這樣60%煤電的系統完全是兩個平行世界。人們印象中光伏非常多的山東省,其容量僅占總容量的25%,電量比例仍然在個位數水平。而大部分省份,光伏還遠遠未到消除中午高峰負荷(13點左右)的地步,更不要說將其變為低谷(圖2,浙江省與加州的日發電結構比較)。

圖2 浙江與加州的日發電結構比較,4月23日
來源:加州2023年4月23日CAISO市場運行數據
浙江為基于負荷與出力特性、經濟調度原則的模擬結果,來自卓爾德項目結果。
系統影響方面。深谷電價的推行,在經濟價值方面影響了新增光伏,大幅調整的用電曲線使得中午的用電負荷增加,避免了可控機組(主要是煤電)的進一步深度調整。原有的高峰時段(比如下午到傍晚)負荷下降,系統平衡的確更加容易。
最后這一點,在目前的煤電出力不足形勢下尤其具有意義。據有關文章闡述:近年來,由于國際電煤價格持續攀升,煤電企業燃料成本大幅提高。按照一臺60萬千瓦煤電機組測算,并網發電虧損約70萬~100萬元/天,遠超非計劃停運考核費用,因此部分發電企業【寧可延長故障搶修時間、承受考核,也不愿并網發電】。
據非正式消息,在保供的形勢下,我國的“容量保障機制”是讓電廠盡可能全力發電,以消除發電激勵不足、以停機檢修為理由避免虧損的沖動。這完全優于容量補償的其他機制,確保“表現”(performance)不用額外支出。
只不過,這么多的好處,讓光伏受損的可能進一步加深了。
聚集案例:浙江峰谷電價與實際發電成本的一致性
我們基于既有的項目研究基礎,以及相對可得的數據,聚焦分析浙江省的峰谷電價及其與實際系統分小時供電成本的一致性程度,來理解午間的極低電價的經濟損失方面的含義。

圖3 浙江終端峰谷電價安排(1-10kV用戶)——中午11:00-13:00是深谷電價
注釋:由于目前的終端電價月度變化較大,絕對值僅為說明作用。
2023年9月開始的峰谷電價安排,低谷電價大工業220kV以上為0.2744元/度,低壓段1-10kV一般工商業用電為0.4235。這一終端電價減去“成本倒推”為基礎的輸配電價,意味著上網電價在浙江的這兩個小時僅在0.15-0.2元的水平。這完全無法對應到任何煤電邊際機組(即使它再先進,效率再高)的成本上。
從規范理論上講,人們的用電行為存在各種外部性,比如污染與全球溫室氣體成本。這些因素構成了電價上升的支持性因素。如果考慮到這些因素,中午極低(其他時間過高)電價造成的潛在社會損失可能更大。
基于Python + Pypsa + Google Colab的開源模型,我們對浙江省電力系統可得發電資源(包括不可調的外來電)2022年的最優開機組合情況進行了模擬,其逐小時價格變化可以代表“應然水平”(上圖藍線)。
從相關系數上講,2022年的峰谷電價安排與全年平均的相關系數在0.5,顯示了這一峰谷安排相比固定不動的基準電價更具優越性。
但是,夏季中午仍舊是(凈)負荷的相對高點,而不會低到人們想象中可再生能源成為邊際機組的情況。即使考慮到光伏的出力最大,由于中午需求的高漲從而一些低效率的煤機都反而需要更大程度開機。在7月14日電價最高的時刻,是這部分煤機決定用電的社會邊際成本。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作為一種動態電價的近似,峰谷安排在月、季節會有更大變化。但是總體上,在比人們想象的更長的“短期”內,中午的需求仍舊是高峰需求。
相關群體動機分析
為何這一午間的超低谷電價能夠實施,盡管其明顯低于了社會實際成本?這涉及我國相關群體的動機與能力問題。下表我們匯總了處在互動中的各相關方的格局。

從上表粗淺的分析來看,這一“超調”的峰谷電價,對不同的相關方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從長期來看,這種粗尺度的價格模式對電力系統的轉型升級并不是最好的選擇。
對下一步電改深化的含義
必須強調的是:峰谷電價、分時電價是改善的電力定價機制,是存在進步意義的。因為不同時間發電的邊際社會成本是不同的。理想的電力定價體系,應該反映這一成本現實。
但是,魔鬼往往在細節。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煤電還維持在發電量60%、大部分煤電在60%-100%之間免費調節、利用率普遍也在60%以上的系統,我國的“應然”峰谷電價,可以預料地沒有想象中的波動那么大。如果超過這一程度,那么價格機制就存在一定優化的空間。
我們可以討論很多技術上的細節,比如現貨市場如何設計、電網公司收入上限如何設定等等。但是,如果不解決深層次的體制問題,這些設計與設定將都是“有偏”的。這是體制改革,而不是機制補充或者政策變化為何更重要的基本原因。
解決體制,必須到了把問題“放到桌面上來”的時候了。近日,有消息稱:政策層面要推動分布式新能源上網電量參與市場。這幾千瓦幾兆瓦的小項目,相比動輒100萬/500萬的大型新能源項目,簡直就是螞蟻跟大象的關系。
后者享受著標桿電價的保護,而前者現在反而要探討市場競爭機制了?巨大的不成比例的交易成本誰去承擔啊?讓我們拭目以待這會是另外一場權力的游戲,還是負責任的政策機制設計。
(作者供職于卓爾德(北京)中心 & 世界資源研究所(WRI))
 微信客服
微信客服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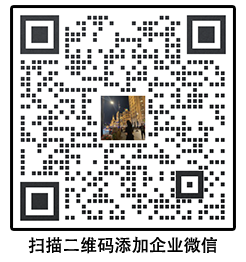









0 條